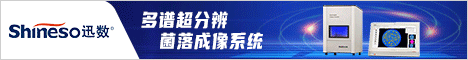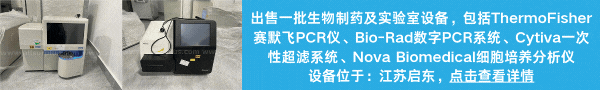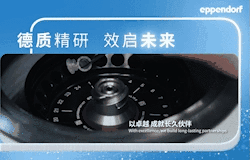納微江博士參加臺灣色譜會有感——圓夢寶島臺灣
圓夢寶島臺灣
閩臺相隔跨時空,
日漸月染憑欄中。
借得微雨溫潤意,
青萍之末乘東風。
---題記
時值2017年國慶、中秋雙節之際,本人有幸赴臺參加“第三屆制備層析色譜技術與應用研討會”,作為與臺灣只有一峽之隔的福建人,年過半百第一次踏上寶島,也是第一次作為大陸方面的專家跟臺灣同胞交流色譜技術,不由心生感慨,同時勾起對往昔眾多臺灣朋友的懷念以及針對兩岸的經濟、政治關系發展與變遷的感悟。
—— 江必旺博士

臺灣高雄郊區小鎮
兒時對臺灣的認識
我出生在福建閩北地區的一個小鎮,自記事起,便知道福建是當時祖國解放臺灣的前線陣地,村子的許多墻上,都寫著“深挖洞,廣積糧,解放臺灣,統一中國”等帶有時代印記的標語。那時的孩子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臺灣人民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解放臺灣、統一中國是我們光榮的使命。
小時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長大后能參軍,這樣就可以有機會參與到解放臺灣的偉大壯舉中。在那個年代,若村里誰家有親戚在臺灣,很可能會成為被批斗的對象,因為那里到臺灣的親戚基本都是參加國民黨的,所以即使真有親戚在臺灣國民黨任職,人們也都不敢承認,實在掩蓋不住的,就發誓與對方劃清界限。這便是來自兒時年代的久遠回憶。那時兩岸是敵對的,近在咫尺卻水火不容。
對臺灣認識的轉變
改革開放后,兩岸開啟破冰之旅。國家出臺相關政策,允許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村里也陸續有臺灣親戚回來探親。記得有一次,村里人都在議論說誰家一位臺灣親戚來,帶回來了許多沒吃過、沒用過的東西,離開時還給留了很多的錢。孩子們都開始羨慕有親戚在臺灣的村里人,兒時的我也曾幻想自己能有個臺灣親戚。隨著兩岸關系的改善和往來的增多,大家慢慢發現,其實臺灣人民并不是我們原先想象的那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是比中國大陸富裕很多。于是對臺灣開始由新奇、交往,到了解、接納,甚至有點兒向往,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就好像原本在村里的兩兄弟,一個在臺灣一個在大陸,幾十年后相見時,在很多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這是八十年代初期,臺灣兄弟不僅在經濟上比大陸兄弟富足,而且在文化教育及人文素養上都優于大陸兄弟很多。
一紙臺屬證明的重要性
1984年我考上了北大之后,自費留學火熱起來,大家紛紛學英文、背單詞、考托福和申請出國留學。那個時候的大學畢業生還很稀缺,上大學費用也基本由政府買單,培養一個大學生需要國家花不少錢,當時由于美國和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巨大,出去留學的學生最后選擇回國的少之又少,即使拿不到綠卡也要想辦法留在美國。因此當時政府不鼓勵大學生畢業自費出國留學,也出臺了一些限制性政策,其中一條就是大學畢業之后必須在國內工作滿5年才能申請出國,但是特別規定在港澳臺有直系親戚的學生除外。于是,一紙臺屬證明在當時特別寶貴,許多想出國的人為了能辦一張臺屬證明去找各種關系、想各種辦法,憑空偽造出不少虛假的親屬關系,因當時兩岸信息不通,很難調查真假。記得當時自己也追著父母親問是否有親戚在臺灣,最后還把外公的弟弟被國民黨抓去臺灣這事也挖了出來,只可惜一點音信也沒有,只好做罷。不過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歷史畢竟在進步,由最初臺灣有親戚的戰若寒蟬,到誰家有臺灣親戚被羨慕,再到臺屬證明對出國留學的推動作用。而且當時出去的一批早期留學生在美國打拼多年后大多成為各自領域的頂級人才,現在有很多被人才引進政策所吸引回國創業,積極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做出重大貢獻。
留學期間的臺灣同學:當時眼中的“富二代”
在美國留學期間接觸到很多臺灣同學。大陸留學生與臺灣來的學生對比可以反映出當時的大陸與臺灣在經濟條件、文明素質及宗教信仰的差異。給我突出的感受是臺灣把中國良好的文化傳統繼承了下來,他們大多數文化素質較高,待人接物彬彬有禮,非常有禮貌。然而可能因為教育體系、經濟條件的差異等因素,總感覺很難像跟大陸朋友那樣隨便和親近的交往。在學校認識了幾位臺灣學生,其中一個還娶了大陸的女生,他們確實是因為愛情走到了一起,而且夫妻恩愛,女方也是中國大陸的名門閨秀,但男方家庭對娶大陸女孩還是有些偏見。
我在美國留學讀博期間,組里有一位來自臺灣的同學,他是我近距離長期接觸的第一位臺灣學生,是我們心目中的“富二代”,在很多方面與大陸同學都有差異。
生活條件的差異是巨大的:這位臺灣老兄住的別墅和生活條件是我們當時做夢都不敢想的,他來美國留學不僅自己掏學費,還在校外住獨棟別墅,條件比我們導師都優越,也讓我們大陸來的這些“窮學生們”大開眼界。當時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基本依靠學校獎學金或去中餐館打工生活,家里根本出不起這些費用。在80年代的國內,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月工資還拿不到一百元,到90年代初也幾百元左右,在美國留學拿到獎學金的留學生,每月領到的生活費就有1000多美元,在國內就是“萬元戶”的級別了。有的留學生一家三口都依靠一個人的獎學金生活,還要再想辦法節省一點錢來資助家鄉窮苦的父母,當時在美國隨便省一點錢寄回老家,對家人幫助都很大。在那個年代,大多數大陸留學生基本都省吃儉用;甚至到美國做訪問學者的國內教授,為了多掙些錢也會去找機會在美國打打工。
當年大陸留學生租的是最便宜的公寓,經常好幾個留學生共租一套公寓, 連床墊也基本是撿來的,一般老留學生知道哪里可以撿到好床墊,于是會帶新留學生去撿。吃的用的也是最便宜的,我們一開始去美國超市看商品價格時,總會把美金價格換算成人民幣,再對比國內物價,一看都是這么貴,因此幾乎是什么便宜就買什么。當時有一位老兄,剛到美國時看美國超市雞腿賣得很便宜,于是每天買雞腿吃,來美國后幾個月就胖了幾十斤,還跟我們開玩笑說把自己也吃得像雞腿了。但即便是這樣,我們這群大陸來的留學生們也已經很滿足了,因為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生活條件相差的太大。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也就是美國普通人有了工作后的正常生活條件。這就是時代的發展和變遷給人的眼光和心態帶來的變化,從中也可看到中國這些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巨大變化也體現在當時中美的物價差別上,80--90年代中國的物品比美國便宜很多,當時每位中國學生出國前都是把能帶的生活用品塞到兩個巨大的箱子里帶上,到了美國后除了吃的需要購買外,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是從國內帶來的。有意思的是20多年過去了,很多事情都顛倒過來了,現在不管是去留學的還是出去玩,基本上不從中國帶東西到美國,而是大箱大箱從美國買東西回來,而且還感覺美國東西物美價廉。
奮斗精神的巨大差異:現在中國大陸很多家庭也都像這位臺灣老兄的家庭一樣,有實力供養家里小孩去美國自費上大學,父母還可以幫助子女在美國買車買房。但在當時,大陸學生都非常羨慕這位老兄的家庭條件。然而凡事都是雙刃劍。正因為生活條件好,據說他的父母承諾不管他多久能拿到博士學位,只要在學校學習就會一直供養他,因此這位老兄也不急于畢業,對學習、做實驗不熱心,卻非常熱衷教會活動,熱心幫助同學、朋友,有時還帶領教會兄弟姐妹在實驗室做禮拜。說實話,這位老兄能在組里混到博士畢業完全是因為他人緣好,要不然可能很難畢業,組里就有一個美國學生混了3年沒有做出任何東西,后來被老板趕走了。
而當時大多數大陸來的學生包括我都想在美國留下來實現美國夢(即實現所謂的3P:Ph.D, Permanent Resident, Permanent Job),因此都非常勤奮地念書做實驗希望早日畢業,早點找到工作。因為我北大畢業后留校工作了6年,在做實驗和獨立科研能力方面得到較好訓練,同時由于畢業壓力大,自我驅動力強,科研結果就比較多,發表文章也多。為了幫助這位臺灣老兄,我特意讓他參與我的研究課題,然后把他的名字也放到我發表的文章里面。畢業后還把沒有完成的一些課題交給他,只要稍微補充一些數據就可以發表一篇第一作者的文章,再加上其它幾篇第二作者的文章混個畢業就應該沒問題。可我畢業后很長時間那篇文章也沒有出來,也不知到這位老兄是怎么做的。在我畢業后做了2年的博士后,接著又工作了1年,跟老板一打聽,臺灣老兄還在學校里,看來家庭條件太好也有副作用。現在大陸很多學生到美國留學條件都非常好,不少家長給子女在美國買豪車和別墅,只是現在很多留學生早已沒有了早期留學生的那種奮斗拼搏的精神,因為早期留學生自己心里清楚要想留在美國實現美國夢必須靠自己的努力,而現在的很多學生父母都給鋪好了路,不需要奮斗就會有很好的生活條件。
在美國工作時的臺灣同事:由昔日工作同事成為今日事業伙伴
我做完兩年的博士后之后,被一家大公司研發中心聘為研究員(Senior Scientist),該中心有不少華人。職位做到較高層的華人大多數都是來自于臺灣或香港,因為他們去的比較早,年齡也比較大。大陸來的都是較年輕的,資歷比較淺,因此在公司的職位也不高。剛開始來自臺灣的華人在公司占絕大多數,但新加入的大都來自大陸,因此大陸來的華人在公司慢慢由少數人變成大多數人。
究其原因,一方面跟中國大環境有關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出國留學政策由緊變松,每年出國的留學生都有大幅度增長,北大、清華等名校都成為留美的預備班,本科畢業的大約一半以上都到了美國,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大陸居民越來越富裕,留美學生越來越多,留學年齡也越來越小,以前需要拿到本科畢業證書后才能申請留學,而如今很多高中生不需要參加高考就可以對接美國的學校去就讀本科,甚至不少初中生都可以送到美國讀書。現在很多留學生也跟我當時的臺灣老兄一樣,家里不僅給交學費,供生活費,有的還給買房買車。而臺灣則與大陸相反,越來越多臺灣留美學生回流到臺灣,而且愿意去美國讀書的也越來越少。另一方面,臺灣為了發展經濟,70-80年代建成了一些工業園,如新竹工業園就是一個典范,吸引了一批在美國有豐富工作經驗且掌握一些核心技術的人才回到臺灣,這些人帶動了臺灣電子產業的騰飛,使臺灣變成亞洲四小龍之一。現在中國也開始學習當時臺灣的做法,積極吸引優秀人才回國創新創業。
在美國工作幾年后,發現想做的科研項目如果不符合公司短期利益就不會被批準,而公司感興趣的科研往往都是‘短平快’的項目,大多數項目基本上也都是產品改進,要求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因此科研人員很難在一個領域做出很深的研究,員工做得好或壞與公司整體發展沒有太大關系。自己想做的比較前沿的項目,若是需要的時間較長基本是無法實現的;因為每個部門的副總每5年就要輪崗一次,因此對花費時間太長的項目不會感興趣,很多美國人比我們清楚自己干多干少與公司總體發展沒有什么影響,因此他們很多人經常是多動嘴、少動手、善于玩辦公室政治。在這種氛圍里很難讓自己成為一個領域的頂級專家,再加上其它原因,我毅然下定決心辭掉工作回國創業。
在美國工作期間認識了一位來自臺灣的資深研究員同事,當時他已在公司工作了十幾年,職位是Principle Scientist,是我見過的做科研最嚴謹最認真的科學家之一,開發了很好的研究方向。我和他雖不在一個部門,但因研究方向和興趣走到了一起,并成為很好的朋友。這位臺灣同事見我毅然放棄了好多年努力實現的美國夢(獲得博士學位,有美國綠卡,買了一棟別墅,生了小孩),雖然不是大富大貴,生活也是非常安逸的。居然拖家帶口把很多人羨慕的工作辭掉,毅然帶著全家回中國很是吃驚和欽佩。他告訴過我,他年輕時也曾有過想出去創業的念頭,一直沒有決心和膽量,最后變成了一個遺憾,因此以后只要我有需要,他一定愿意來幫我。后來事實也證明了,兩年后他也提前辦了退休和我回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組建微納米材料研究中心,后又跟我一起到蘇州創業。即使這位老兄對大陸空氣污染過敏,生活不習慣,卻一直堅持留在中國跟我一起創新、創業,直到今年由于年齡原因拿不到工作簽證才返回美國與家人團聚。通過他我也了解了很多臺灣真實的情況,但一直沒有機會跟他一起去臺灣看看,實屬遺憾。
這位老兄身上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品質,做什么都一絲不茍,干凈整潔,待人接物甚是禮貌,尊重所有人,不管職位高低,甚至對餐廳師傅都彬彬有禮,每次用餐都會夸贊食堂師傅,從美國探親回來后還會給食堂師傅帶小禮品,使得師傅受寵若驚,因此對這位老兄也會有特殊的照顧,即使我是公司的老板也只有跟這位老兄一起到食堂才可能享受到食堂特殊的待遇;這就是大家說的尊重別人也就是尊重自己,這種高素質也是中國大陸越來越稀缺的。公司所有員工對這位老兄也都很尊重,甚至連房東對他也非常滿意,起初房東想把房子賣掉,后來租給了這位老兄,與我們大多數人租房子不同的是,這位老兄比房東自己都愛護房子,每天把房子打掃得干干凈凈。 房東看后放棄了賣房的想法,在蘇州的6-7年間他也就一直租住這個房子,房東因為這位老兄的原因,不僅掙了多年房租錢,也趕上蘇州房價翻了幾倍,房子價值多了幾百萬人民幣,我想房東一定對這位老兄非常感激;其實,這就是素養品行、與人為善的好處。大陸經濟發展了,也希望中國這種傳統的優秀品質可以形成。
來自臺灣的鄰居
在美國參加工作后買了一幢全新的別墅,實現了剛留學時想都不敢想的夢,我所在的小區一共有6家華人,有5家來自國內,所以很快就熟悉了起來,只有1家是兩岸結合的夫妻,男方來自臺灣,女方來自大陸,他們生活比較西化與獨立,可能是以前與大陸來的人產生過不愉快,所以對大陸來的人有些偏見,也不愿意與大陸人交往。后來我們家小孩經常到他們后院草地上玩,他們對小孩很好,慢慢就熟悉起來,對大陸人的偏見也在慢慢消失,最后變成很好的朋友,看來天真無邪的孩童最容易破冰。
深度交往后才了解到,這對兩岸結合的夫妻其實非常能干,也非常樂于幫助人,他們自己房子的Deck和地下室裝修都是他們自己做的,我們幾家大陸來的后來也都跟著他們學習自己建Deck. 我們回國后,房子打理都交給他們倆,包括出租房子和修理房子給予了我們很多的幫助,如果不是他們熱心幫助打理房屋我們應該早就把房子出售了,直至今日我們回美國時也經常會住在他們家里。每次去,他們都把鄰居幾個華人聚集一起舉辦聚會活動,因此心里一直非常感謝這位鄰居朋友,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他們也很感激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們讓他們能更加客觀的了解從大陸來的留學生,并消除了以往的偏見。
夢圓臺灣之旅:學術交流 實現兩岸共同合作
這次真正踏上神交已久的臺灣,要特別感謝意守大學的梁明在教授。我和梁教授都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并從事共同的色譜領域,他的專長是做連續色譜系統,我的專長是做色譜填料,具有很好的互補性。這些年梁教授一直致力于色譜技術在臺灣的應用推廣,并連續3年在臺灣成功舉辦了層析色譜技術研討會。而我回中國后也一直致力于色譜材料的產業化,并連續在大陸舉辦4屆制藥分離純化研討會。這次很榮幸成為唯一一位赴臺參會做報告的大陸同胞代表并與臺灣色譜屆進行深度交流。

臺灣意守大學校園景觀的一角


第三屆制備層析色譜技術與應用研討會報告現場
學術會議在意守大學舉辦,這所學校由臺灣的企業家捐款建成,建筑風格很像美國的大學,參會人員就住在學校的酒店里。梁教授任會議主席,校長到場致辭,表示兩岸尤其是學術界應該進一步增加相互了解和交流。因臺灣從事色譜研究的教授非常少,因此舉辦方邀請了包括張玉奎院士在內的幾位大陸色譜界專家,但遺憾的是這些專家最后因為沒有拿到入臺簽證無法成行,而我因為是美國護照得以順利參加。相信如果大陸專家到臺灣做學術交流,能夠像臺灣同胞在大陸做生意一樣自由進出,那么這次會議的成效會更好。

與臺灣色譜會議演講嘉賓合影
今年是臺灣第三次舉辦這種會議,參會的只有一百人左右,規模較小,由于預先準備的演講嘉賓大都是來自大陸的,后來臨時改成臺灣演講嘉賓,總共也就5位。我們今年9月份在中國蘇州舉辦過類似會議,參會有500多人,演講嘉賓有30多位,而且有從美國專門趕來參會的華人色譜專家,規模及影響力都很大。梁教授也參加了我們舉辦的會議,感嘆臺灣色譜界和大陸相差太大,既沒有市場也沒有人才。通過深入溝通交談,我和梁教授達成共識,要共同推動兩岸色譜技術的進步,在各自自發在大陸和臺灣舉辦制備色譜會議基礎上,爭取明年能合力共同在大陸舉辦一場兩岸制備色譜會議,以促進兩岸的生物制藥產業的交流、發展。

第四屆制藥分離純化技術與學術大會現場盛況

納微科技承辦第四屆制藥分離純化大會部分嘉賓合影
上午做完報告后我還應邀參觀了梁教授的公司,順便了解了臺灣創業的環境及目前大學生就業的待遇情況。結果出乎我的預料,臺灣大學生剛畢業的工資也就每月5000元左右的人民幣,與大陸發達地區基本沒多大差別,遠低于美國、韓國和日本。想想臺灣曾經是亞洲的四小龍之一,又有大陸這么大的市場,但近幾年臺灣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產業優勢早已被韓國趕超,臺灣經濟發展不利是否和本身政治體制或是本身體量小等原因有關就不得而知了。
臺灣高雄的房價比上海、蘇州便宜很多,每平米的均價在1萬元人民幣左右,通過對比也可以看出中國房地產的泡沫;由于臺灣人口基數小,市場小,創業也不容易,能做大的企業都必須要走出臺灣,如富士康等。梁教授同時很羨慕我們在中國大陸創新、創業的環境,不僅政府支持,而且國內有大量的人才和巨大的市場及完整的產業鏈,足夠把企業做大做強,當然在國內做公司也有很多不利的因素,如競爭激烈,人才流動頻繁,稅負重,政策變化快,市場不規范等等,相信這些前進中的問題,會隨著新時代的進步逐步得到改善和優化。
這次臺灣舉辦的制備色譜會議剛好是安排在國慶和中秋雙節期間,并且也臨近臺灣的雙十節,本打算在臺灣多呆幾天,以便可以多了解些臺灣的行情,但由于飛機票非常緊張,最終只在臺灣呆了一天一夜。
感想與后記
大陸、臺灣,兩岸同種同宗,因政治因素的分離,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道路,也造成了兩岸人的思想認知和文化素養上的差距。幾十年的發展變化,從臺灣經濟優先崛起成為富親戚,讓大陸百姓羨慕,到近年來大陸經濟后來者居上并擁有全球最大市場和人才,也讓臺灣民眾羨慕,可謂滄海桑田,世事變遷,唯有中華民族血濃于水的文明淵源流長,心靈契合。我想,增進了解,互為體諒,取長補短,是大陸與臺灣民眾成為朋友的關鍵。和平共處,互相促進,共同提高,一定會是雙贏的局面,也是兩岸人民的福祉。
兩岸民間經濟往來已經很順暢,且成果卓著。作為國內科技創新企業,納微希望今后能夠進一步加強兩岸科技往來,促進學術界特別是高科技成果之間的資源共享、技術研討與交流,集合兩岸力量,共同推進色譜技術的科研水平和市場應用,進一步打破國外產品的壟斷,讓更多的國內企業分享最新科技成果的紅利,同時兩岸科研攜手,共謀、同創民族科技復興之偉業,登上世界色譜分析與應用技術的巔峰!
致謝:
誠摯感謝我北大的老同學江慶紅及納微科技的卜繼國、崔賀卿在本文章撰寫過程中的協助。
江必旺 博士
于2017年10月
江必旺博士簡介

1988畢業于北京大學化學系,獲紐約賓漢頓州立大學博士學位,加利福尼亞伯克利大學博士后,2000年加盟美國Rohm&Haas公司任資深研究員,曾獲1999年美國化學協會化學界Zappert Award 獎。2006年到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創立納微米材料研究中心并入選廣東省重點實驗室。2007年創立了蘇州納微科技有限公司,從事高性能精準色譜填料及層析介質研究與產業化,開創領先的單分散硅膠和聚合物色譜填料技術,成功出口歐美、日韓等國,打破中國長期單向進口的局面,發起成立醫藥分離純化產業聯盟協會,入選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007年獲蘇州工業園區首屆領軍人才,2017年入選科技部2016年創業創新人才。
- 百蓁生物邀您共赴CBI 2025生物醫藥創新博覽會
- 明美光電首屆蘇州經銷伙伴大會圓滿舉辦
- 中國醫科大學功能超聲fUS成像儀ICONEUS ONE成功裝機
- 上海優耳儀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20周年答謝函!
- 覃思科技成為丹麥DeltaPix顯微成像產品中國區代理商
- 易科泰創新實踐國家發改委“百城千企”課題
- 盧湘儀離心機亮相央視,國產科研利器賦能經濟發展
- 贊德公司關于美國Med associaties中國獨家代理聲明
- MCE推出AI藥物篩選平臺,實現數千萬的分子快速篩選
- 迪必爾入選2025關鍵技術研發計劃"合成生物學"項目
-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宣布停止對僅動物研究的資助
- 智聽自然,聲動未來:沃德精準亮相"聲景中國"研討會
- 赫西智能高速冷凍離心機亮相央視"革新人工催產技術"
- 易科泰榮膺“SFAA 植物工廠應用十大優秀企業”稱號
- 百蓁生物推出一站式高精度HDX-MS分析服務
- 博格隆精彩亮相CPHI & PMEC China 2025
- 博格隆將攜明星產品亮相CPHI & PMEC China 2025
- 相約成都:博格隆邀您參加2025未來XDC新藥大會
- 博格隆精彩亮相BIOCHINA2025第十屆易貿生物產業大會
- 相約蘇州:博格隆邀您參加BIOCHINA2025
- 博格隆蟬聯2024中國生命科學服務企業品牌100強
- 研討會:抗體類藥物下游純化工藝關鍵要素解析
- 博格隆7款明星層析填料產品限時免費試用,先到先得
- 博格隆推出抗體純化新品AT Protein A Diamond Ultra
- 博格隆官網煥新上線,服務體驗全面升級
- 正民德思獲西班牙純化填料廠商ABT中國獨家代理權
- 博格隆邀您共聚韓國BIOPLUS-INTERPHEX制藥展覽會
- 博格隆獲生物創新藥領域本土原材料年度卓越供應商
- 博格隆與您相約德國阿赫瑪博覽會ACHEMA 2024
- 博格隆榮獲嘉興市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能力百強